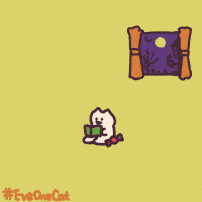爷爷的狗(二)
说到狗,其实那条肠胃不好的,并不是爷爷的第一条,在他之前便已经有六条了。他们之中有病死的,有被偷的,有出车祸的,有养了一半送人的,还有偷跑出去走丢了的——这狗多半是个路痴,但也不能怪狗,毕竟他们能够外出的时间仅仅是他们一生中的多少分之一,多少分之一呢?也说不上来了。
若是说那不同寻常离世的狗是因为走了霉运,不提就不提了。但那卖掉的狗就不得不说一下,因为他们本可以安度晚年的。那是一只最凶狠的狗,我甚至曾经怀疑过它是不是吃狗奶长大的狼,同样它也是唯一参与了我童年,留下过痕迹的那一条——包括在我的手指上。
至于它的由来,我也记得不太真切了,但仿佛是爷爷从他的一个朋友那里要来的——爷爷的朋友很多,这总能为他在某些场合博取一些资源——尤其是那些猫猫狗狗的那些事儿上。就这样,那条又瘦又小的它,就进入到我们生活,和我一同成长。
渐渐的,它越长越大,也越长越凶猛。它的狗窝是安排在茅厕附近的,这会带来一个麻烦事:人们都不敢去上厕所。于是亲人们回来的时候都会叫我给给他们看着狗,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,便那一张铁锹轻轻的抵在它的嘴巴旁边,它便乖乖的了。一旦走开,它便像一匹饿狼一样咆哮着,不停的啃食嘴边的木头。时间久了,木头开始泛黄,但一旦有人来串门,它便开始磨砺着新的颜色。
人们都说:你家养了一口狼。
是啊,我家确实有一匹狼。
关于它的故事,并没有特别精彩的部分,但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,我却记得尤为真切:那段时间家里刚刚安了机顶盒——这是这个小小的盒子,但里面却藏着不计其数的节目:神厨小福贵,虹猫蓝兔奇侠传,喜羊羊与灰太狼,大耳朵图图,数码宝贝……那些节目可不是仅一个山西卫视可以包揽的。再者说,家乡的电视台无时无刻播放着不是《西游记》就是《大戏台》——这在那个时候充满童真的眼里,可不是件好事。
唯一叫好的,就是爱看戏曲的爷爷奶奶。我会把所有的动画节目频道调在最前面,那样会占据了CCTV相关频道的位置——这种技能在家里可是只有我会,我会得意的只拨动上下两个频道键就可以博览所有的动画节目,以便在一档节目插入广告时迅速跳转。但爷爷奶奶就不一样了,遇到好看的频道,他们刻意的记忆该频道的位置,常常奶奶会问我:“亲(qìn),咱们叶 [yè:昨天的意思] 儿黑夜看的那个电视是在几台了? ” (亲,可不是淘宝体专有的词,在我们这里长辈对晚辈的爱称就是这样叫的)这个时候我便会故作烦躁的拖着下巴,“奶奶你看,你按一个五,按一个七,这样一下子就跳转到那个台了。” 这个时候奶奶便会戴着老花镜,颦起眉头,摸索着五和七的位置。找到之后便会按照我说的去按一次。
若是找到了,奶奶便会来一句:“看俺娃精明的”;若是没找到,便会再来问我:“这咋了不是昨天演的那个电视”。这个时候我一般会回一句:“奶奶你等一下么,它慢慢就演的接住了。” 之后,奶奶便会若有若无的“嗷”一声。等到我手中的漫画看完之后,悠然抬起头看着电视传来一句:“你这个大骗子!” 定睛一看,电视里全然放映着另外一个频道——原来奶奶按的时候太慢,在跳转之前还没有摁另一个键,结果就跳转到五频道了。大多时候是这样,但也不排除某些时候我“ 喜提新道 ”,又重新调整了频道的顺序。若是后者我便会暗暗将那个错误的顺序调整到兼顾的状态,顺序是解决了,但句 “你这个大骗子!” 仿佛一直在责怪我没有及时抬头。那个时代,一个频道,一把瓜子,头顶上忽明忽暗的灯光,电视里忽大忽小的声音,便是饭后最大的快乐。
要说因为看电视产生的矛盾,那也是有的,只不过常常发生在我和爷爷身上。爷爷钟爱他的新闻,我偏爱我的动画。早上七点钟是每天新闻诞生的最早时刻,但那也是《马丁的早晨》更新的最早时刻。爷爷说,新闻看重播就没意思了,那样就不新了;我说,马丁的早晨就是要早晨看的,中午那就成马丁的中午了。似乎都有道理,双方都不肯让步,但是论讲道理,比力气,我可都比不过爷爷。反正过程记不清了,但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梨花带雨地跑到了院子里。那狗不知所措的看着我,我一边啜泣,一边拿着盛放狗食的大勺子——那是爷爷那一辈人用的剩下来的,一边拿勺子凿着地,一边小嘴诅咒着停电。啪!清脆的一声,勺子断了,电也停了。
我愣愣的拿着剩下的半个狗勺子,茫然不知所措。看不成新闻的爷爷踱步走出家门,看到院子里犯罪现场,再加上看不成新闻的恼怒,气冲冲的跑过来:“巴你个灰鬼!”一双粗糙有力的大手打在我的后脑勺上面。这下水龙头关不住了,哇的一声便排山倒海地哭了。这时狗仿佛在为我出头,汪汪的不停叫着。似乎觉察到异常,奶奶应声而来,看到哭的不成样子的我,奶奶嗖的一下冲过来抱着,狠狠地瞪着爷爷:“牲口!” 再后面发生地事情便浑然记不清了,但从那以后,我对我家的狗便格外友好,常常会故意剩下一大块肉,咬一大口便不吃的烧饼,藏在汤里面的小排骨…..但后来我发现这些东西并不能到狗狗的嘴里,在那之后我便私下给狗狗改善伙食了。后来我提起那件事,奶奶便会笑着说:“你看你爷那个时候灰了 [在我们这里,灰是坏的意思] 。” 但是爷爷便会惊讶道:“啊?啥时候的事,我还打过小娃了?没了 ” 说罢,便戴着帽子便迅速离开了。
我不曾记着它的到来,但是它离开的时候我却格外的清晰。至于原因,那便是我从小落下的湿疹——大夫说,除了牛肉龙虾,辣椒韭菜,狗毛也是重要过敏原,尚且狗身上的跳蚤也是你长期瘙痒的重要原因。或许是被那疾病折磨了罢,或许在不想忍受中药那苦涩的味道。家里人一商量,就决定把狗买了。爷爷起初不愿意,再三思索以后,最终也同意了罢。它离开的那一天,我还在上学,回到家之后,它便永远的离开了。它甚至都未曾拥有过自己的名字,未曾拥有过自己的爱情,从我四岁那年来到家中,直到我十二岁的那一天离开。因为过于凶猛,它能够外出的时间少之又少,它的一生被囚禁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,忠诚又负责,但最后的结果是——我们把它给买了。
后来发生的事,说来也有些荒谬可笑。我的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退去的;第二年爷爷又凭借他的人脉搞来一条狗;奶奶还是兢兢业业的喂着。只不过那时的我去了县里面的高中,爷爷也不在热衷于新闻,奶奶也不在去记那些频道了。她总是看一会儿便换一个台,看一会儿再换一个,再看一会儿,就关了。
村里的狗大多都是一个命运,从出生到老去,他们无不在那个小小的院子里。当然在他们之中也有英年早逝的,也有不幸离世的,真正能够寿终正寝的少之又少。它们从不挑食,主人剩什么,他们就吃什么;他们恪尽职守,谁进来它们就咬谁;他们也从不在乎明天是什么样子,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它们也只是浅浅的睡着,一有动静便会冲着天空长啸。黎明破晓,它们便知道:第二天要来了。那便又会是日复一日重复着相同的事。枯燥却执着,苦涩却英勇。
那便是它的日子,那也是它的生活。